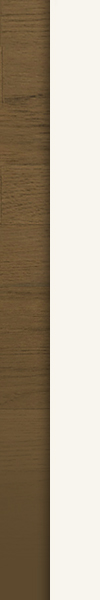說到以前對外公的印象,大概也是外公70歲以後的事了。小時候的我,認為外公是一位偉大的醫生。那時,他住在鄉下的老家,後面是外公外婆起居的住所,前面則是鎮上唯一的診所。過年回到鄉下,如果在傍晚以前抵達這個偏僻的小鎮,看到一家快要關門的老舊診所,診所外懸掛著字跡斑白的木製招牌。如果不是招牌上斑駁的「金河診所」四個字,或許大家都會以為這只是一間被主人遺忘的老舊日式建築。外公有時會在木製診療桌的後面會診病人,有時會因為有客人來拜訪而回到家裡的大廳與人寒喧,不管如何,等到傍晚時分,外公都會到小診所外把木製的拉門拉上。隨著老舊拉門摩擦生銹軌道的嘎滋聲,以及木門上幾片玻璃的搖晃震動,待拉門關上,診所便結束了一天的營業。
或許有人會問「這哪裡偉大了?不就是一位平凡的鄉下醫生嗎?」的確,每次回老家,往往看到外公與來拜訪的客人們相談甚歡,又或者正仔細地詢問那些與他互以姓名相稱的病患各類不適症狀。外公並不會給人相貌堂堂、威風凜凜的印象,或許只是因為他似乎很受到村裡人們的敬重吧?或者僅僅是因為他是我的外公?總之我對外公最早的印象,就是一位偉大的醫生。
過了幾年,差不多在外公80歲前後,外公開始受頒一些關於醫療奉獻方面的獎項,最早是從賴和醫療獎開始,社會開始注意到外公早年前在鄉下替烏腳病做的貢獻。這時,我才發現,外公會得到鄉親們敬重的原因,並不僅僅是因為他一直在村裡經營著一家診所服務大家,更是由於這段歷史淵源的緣故。
外公退休搬到台北居住後,我有了更多的機會與他見面,也更有機會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外公。現在,外公已經92歲,而我也已經22歲了。有人稱外公為「烏腳病之父」、「仁慈者」等,總之有幾個聽起來頗為偉大的稱號,只是,當我偶爾見到外公,凝視外公專心閱讀書籍的身影時,總是無法將這些稱號與他互相連接。原因之一,是因為那些外公被頌揚著的事蹟,是在我還未出生的久遠年代發生的,自然不易有非常深刻的體會。然而,最重要的原因是,對我來說,外公其實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普通人。曾經,外公帶我們去海邊挖牡犡。他買了4把挖牡蠣的小鏟子,分別給我、我媽、我姊和他自己。到了海邊,他先告訴我們挖牡蠣的方法,接著便蹲下來自己挖了起來。在接近黃昏、空無一人的海灘上,只剩下四個詭異的身影在沙灘上挖掘著,像是在進行某種儀式似的。最後,年紀最大的外公挖到最多的牡蠣。然後我們踏上歸途。回到家,外公養的狗用狂吠的方式興奮地迎接我們,然後我們請這些剛挖出來的牡蠣進入攝氏一百度的滾水,燙死之後直接將牠們剝開挖出來吃了,回憶至此結束。
當我回想起這往事,心中並不覺得特別甜蜜或特別懷念。挖牡蠣的感覺很愉快,但與其他和外公相處的時間相比,還算不上是最愉快感動的一次。努力挖掘出來的牡蠣味道早已淡忘,流汗後的充實感也在吃完晚餐不久後煙消雲散。唯一留下來的,是我對外公更深一層的了解。與其說是一位偉大的醫生,我認為外公更是一位忠於自己的行動派。他希望我們快樂,便帶著我們三人去海邊挖牡蠣。早些年前,或許也是因為某個理由(一開始的原因未知,後來或許與謝緯有關),使他毅然投身於烏腳病的醫療工作長達數十年。依自己的原則訂出目標,接著付諸行動,這種誠實面對自己的處世原則,以及發現目標後的行動力,都是現在的我望塵莫及的。
與我們這些孫子相處時,外公很少說出他對我們的要求,只是用正面的話語來激勵我們。過去,我認為這是因為外公不想給我們壓力,所以不好把對我們的期待說出口,而現在,我有了新的想法。或許,外公已經用行為表達出了他對我們的期許─誠懇對待別人,也誠實面對自己。這也是外公最特別的地方。
孫子 謝東澐 |